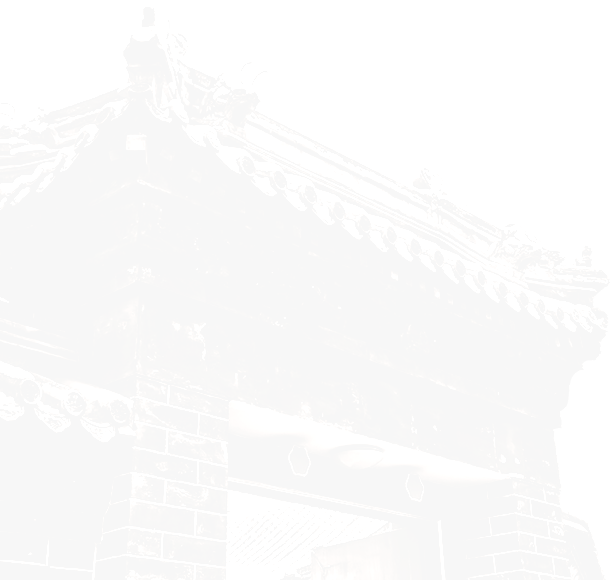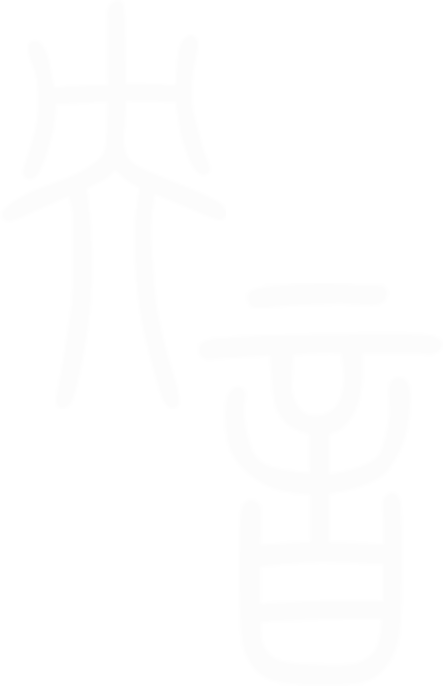2025年3月21日下午两点,作曲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沈叶先生应beat365官方网站作曲系“专家讲堂”系列课程邀请在教学楼617室为2023级博士研究生以及现场的众多老师、学者和学生进行了题目为“二十年,参加一场无终的谈话”的讲座。
沈叶教授首先解释了题目中“谈话”的含义,他将音乐与思想之间的交互称为“谈话”。沈教授对二十世纪美国小说家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1938—1988)的观点:“写作,或是任何形式的艺术创作都不仅仅是自我表达,它是一种交流”深以为然,其自标题交响诗《纪念》(2005)问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音乐创作并非孤立表达,而是与生命、自然乃至思想的交互。在这些交互与联系中,沈教授将自己在周文中先生的音乐和思想中所获得的启发作为本次讲座的重点,并结合谱例与音响从感知敏感度的提高和转化以及选择中的舍弃两个方面展开讲述。

一、感知敏感度的提高和转化
讲座的第一个主题有关感知敏感度的提高和转化。沈教授认为,音乐表达仰赖高度敏锐的感官知觉,其中听觉为核心,也需要与其他知觉协同发展。随着时代的进步,当代认知科学使我们发现,感知能力不仅受生理器官功能影响,思维活动和情绪状态更在其中占据主导,因此作为音乐家必须像练琴一样坚持锤炼自身感知敏感度,同时反思语言、视觉、情绪等因素对思维能力的多方面影响,避免认知钝化。真正的创造性音乐表达必然超越感官的原始条件反射,需经历将感官带来的原始感知淬炼为高级音乐思维,而后整合为有意识音乐语言的三重转化。所以,感知的转化实为初始直觉与创造性表达间不可或缺的桥梁。
接下来,沈教授以周文中先生的作品为例来对感知敏感度的提高和转化进行进一步阐释。创作于1957年的钢琴独奏作品《柳色新》是沈教授所接触到的第一首周先生的作品,作品中的创造性思考寓于诸多细节,至今仍旧令沈教授印象颇深。此外,《柳色新》中独特且入微的音响设计也给予沈教授极深刻的印象,如音响各不相同却均具有极强的不可替代性的低音区小九度震颤,谈至此处,沈教授现场在钢琴上进行了演示。随后沈教授由不同的人对这些震颤的不同反应总结了感知的三个层次,其中前两者有关感知敏感度的提高,后者则关乎感知的转化:其一,大多数人能够对此产生模糊的认知但难以分辨其中细节;其二,在经过引导后人们更易清晰辨别;其三,感知可被音乐家加以转化,从而实现艺术表达。沈教授认为,艺术创作的本质在于对感知和意识的创造性转化,艺术家自身应具有对细微现象的敏感度,也应具有转化其为可传递的审美体验的能力。
在对感知敏感度的提高和转化做出具体阐释后,沈教授就“转化”展开进一步的探究。首先是艺术创作中“离原形近”的转化手法,其目的在于更好地表现原形,转化的具体手段往往奠定作品风格基调。沈教授先以几幅绘画作品为例进行阐释:马远在《华灯待宴》中以游丝般的笔触勾勒山脉,近看模糊,远观则构成云雾缭绕的远山;萨金特的《哈默斯利太太》与《阿伯农子爵夫人海伦·文森特》分别通过光斑暗示蕾丝的颤动轻盈质感和通过排列的色点来暗示珍珠项链的立体感;康定斯基的《旧城》则以断续的色斑呈现阳光下妇人的形象。之后,沈教授重新回到音乐创作中进行举例:柏辽兹《幻想交响曲》体现了离原形较近的转化,作品第四乐章开头低音提琴分部拨奏的G小三和弦,其以极低音区、极弱力度、止音技法及齐奏的细微时间差共同构成模糊的“沙沙”声响(此处音高的选择更多应源于柏辽兹对于调性传统的惯性,而非音响本质需求);梅西安《鸟的苏醒》中的附加共鸣则离原型稍远一些,这种转化比起拟声更偏向纯粹想象,作品通过音色选择和力度控制实现鸟鸣音响的创造性转化,对此沈教授引用了杨立青先生的话:“是强制性改造,作曲家自主的选择。”
接下来,沈教授将“转化”进一步抽象化并开始对自己的创作进行解析,同时也在现场为同学们分享了许多谱例。沈教授首先讲述了自己对泛音的独特感知方式,他用两种时间差方法来捕捉音响中的泛音:一是在基频能量没有完全释放前率先捕捉高频泛音的闪现,二是在强频衰减后从余音中寻找长而弱的泛音,沈教授形象地将这种听觉方式比喻为观察极光时先用余光定位后再聚焦目光欣赏的过程。沈教授注意到,那些泛音在自己的特别关注下会呈现逐渐渐强再消失的过程,但这实际上仅仅是一种听觉感知和心理现象,因为从物理层面上来讲,弱频通常并不会真正渐强。
沈教授将这种听觉感知在创作中进行了抽象转化,即将数十个弦乐长音声部分布在七个八度的广阔音域中,通过其各自独立的演奏法和力度变化产生丰富的泛音与复音音响。这些音群整体运动时的音响变化极其丰富,变化万千,沈教授首次在创作中实现这种转化理念是在为打击乐、钢琴和弦乐队而作的作品《旅行者的梦》(2006)第二乐章中部至乐章末尾。
周文中先生所编瓦列兹“新乐器和新音乐”讲稿中转述了瓦列兹的话:“声音如光的探照灯,声音平面以不同速度和夹角移动,整个是一个整体,如大河奔流……”沈教授对《旅行者的梦》所做的设想正与瓦列兹的音响观念不谋而合。时间推进至2009年,沈教授与陈晓勇教授在汉堡的一次交谈中发现彼此对泛音的“渐强”感知存在共鸣,但转化出的音乐织体却迥异。沈教授在《旅行者的梦》中呈现的极光和弦是广布的绚丽,而陈晓勇的《不可见的风景》则追求空灵的静谧。这一经历引发了沈教授的极大兴趣,他直言:“一个少见的启迪,例如一种聆听和想象,也很可能“击中”不止一个人。因此我不在意这个灵感的来源与他人相同还是不同,来自他人还是来自于自然。只要是一个真正的音乐家,从任何来源生发的创造都能意义独具。”这也启发了沈教授有了“不必当第一”的心态,极大地解放了他的创造力。2014年,通过分析笙演奏家吴巍的录音,沈教授首次观察到其可通过精准演奏控制持续音中“不同分音的交替隐显”现象,这激发沈教授创作了作品《铎》(2015),并在其中用手指略板的记谱和气息压力要求控制三十七簧笙的多音和声里面每个成分音的独立。时间来到2018年和2019年,沈教授又分别创作了《小提琴协奏曲》和《合唱套曲》。沈教授在这些作品的创作中,使用了更为抽象的转化手法,其目的是每一次不同的塑造。
在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一番详尽解析后,沈教授再次回到了《柳色新》的“震颤”之中,沈教授认为那是周文中有意塑造的音响,而音高仅是其诱发条件之一,而听众是否由此联想到古琴则因人而异。他强调,作曲家的天赋——也是职责所在,即使“听不见的”转化为“可听见的”,无论是受自然启发还是他人影响,最终都需转化为创造性的音乐表达。周文中所引述的瓦雷兹的“声音的投射和形状”以及其本人“音的偏移”等观念,都成为了沈教授重要的创作种子。

二、选择中的舍弃
在对感知敏感度的提高和转化进行详细阐释后,沈教授将本次讲座推进至第二个主题,即关于选择中的舍弃。艺术家必须找寻和建立自己的艺术规则,当面对无限可能时要有所舍弃才能有所选择。为了说明这一点,沈教授依旧由周文中的创作理念入手。
首先,沈教授自取舍对个人艺术规则建立之影响的角度进行举例。周文中自《易经》和阴阳哲学中汲取“循环、变化、进展”的抽象规律,舍弃了与命运、吉凶等内容,这种选择性吸收体现了他建立个人艺术规则的方式,也让沈教授感到颇有共鸣。例如,十二平均律的十二音序列有约4.79亿种排列可能,但运用近似周文中在《霞光》(2007)中采用的九音和弦规则(即十二音选九音,且其中必须包含至少一个增三和弦)则能将可能性缩减至220种。再结合黎昭纲(Eric C. Lai)揭示的周文中“填白”方法并结合周文中的音乐世界观,从六音到九音再到十二音,构建独特的层级化音高组织关系。这就是有目的的舍弃,有意味的挑选。
另一个例子则有关术语的取舍与转译。周文中为揭示瓦雷兹音乐与传统间的联系,在术语方面进行了转译,他舍弃了瓦雷兹的术语(如“音群”“变形”),转而使用传统音乐术语(如“和弦”“转调”)来揭示瓦雷兹作品《电离》中音色关系的转换实则是传统音高组织逻辑的代替。
与此同时,周文中对《电离》的音色分类法也对沈教授的音乐研究启发良多。沈教授舍弃了周文中的特性分类(“响弦鼓类”“波浪式发声类”等),而采用新的描述法,如“乐音-嗓音比例”、“谐波分布幅度”、“起振-衰减类型”等的综合与消长。沈教授直言,这种新的描述固然行之有效,却也亟待完善,但自己确实通过“舍弃”自周文中的音色分类法中获得启发并取得研究进展。
再者,关于单音概念,周文中1970年的文章《单音作为音乐的单元》提出“偏移”概念,为醉心于声音运动的沈教授提供了思考方法。比起“偏移”,沈教授更希望用“音响的流变”,“微差化”,“突变与渐变”来作为形容这种声音复杂的微妙变化。沈教授在2015年写作的《微差化研究》中就系统化前述变化手段并展现其不同结构作用做出研究,同时归纳中国1980年以来一些当代音乐的特征。而后,在《声乐中的渐变之美》中,沈教授突出“连续体”概念:即无法抽离出稳定音高的连续滑动音高,或是持续不断变化的音高滑动速度等,这些包括力度、音高、空间等多个因素互相影响,最终形成的独特音响形态。对于“连续体”必须综合多个方面进行把握,孤立地看待它或摘出任何部分都可能导致其变形。
此外,沈教授主张弱化“单音”的概念。沈教授认为其之所以被周文中同时代的人所强调是因为其具有与过去依靠音高变化构成结构的时代的相反特征。单音只是表象,音乐创作最重要仍是创作内容和艺术表达。
最后,沈教授对本次讲座做出了总结,周文中予他以启发,其中包括感知敏感度的提高和转化以及选择中的舍弃,而沈教授在经过长期创作和研究后,证明了这些启发的确对自身有着极大的意义。
在为时90分钟的讲座结束后,沈教授还回答了现场的同学的一些问题。作曲系作曲方向2024级博士研究生文子洋同学提问:“关于您创作中极光和弦的音高选择,感性听觉和工具运算哪个更占据主导?”沈教授对此问题作出解答,他认为音乐创作中的感受永远是第一位的,使用技术手段获得结果固然精确且快速,但正如自己与陈晓勇教授对于同样声音的不同感受和表达会造就两部不同的作品,艺术家的个人感受和为之做出的研究和努力才是独特艺术表达的前提。随后,作曲系作曲方向2024级硕士研究生王天仪同学就沈教授在讲座第一个主题“感知敏感度的提高和转化”中提到的离原型远与近的概念提出问题:“中国传统音乐中对生活中实际音响的模仿是否可以加入您所说的这个概念之中?”沈教授认为这是完全可以的,但讲座毕竟受时间和条件的限制,所以仅挑选了部分作品作为例子对此概念进行了大致的解读。
笔者希望以沈教授在讲座最后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综述:“他(周文中)对我的启发,也是这种影响作用于具体的另一颗心灵的结果。展现这些心灵间的关联,我希望能鼓舞别人。正因为有前人,有无数的后来者,还有再后来的人,源源不断,所以我坚信美好的音乐精神不会断绝,一定代代有共鸣。这是我的幸运,已经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参加这场没有终止的谈话。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我试图在这次讲座中,展现一些比一个人的一生更久,比五年十年的剧烈变化要更加深远的心灵关联。我希望,大家能对持续和高尚的个人努力抱有恒常的信心,发现共同努力的人,他们可能和你有万里之遥,或有千百年之久,但没关系,和他们做朋友吧。”
(撰稿人:刘天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