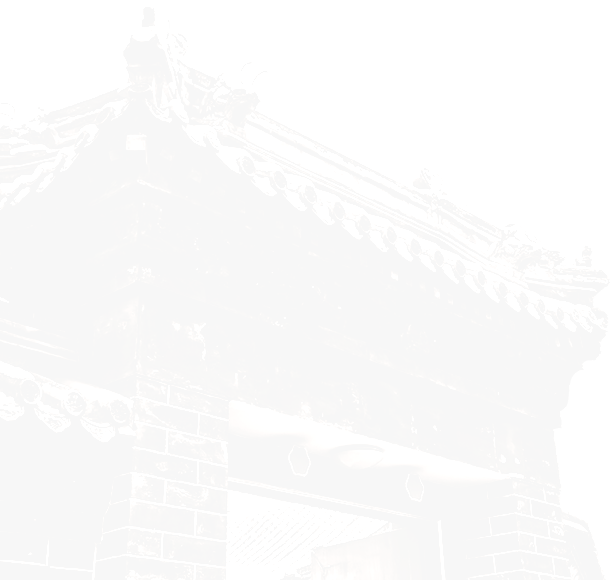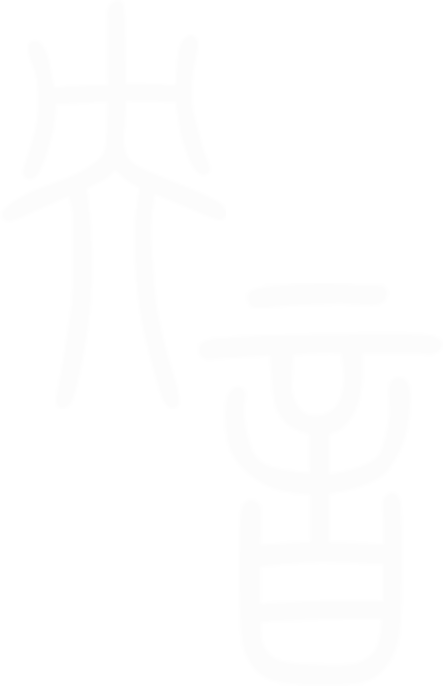2025年3月7日,2023级博士研究生“专家讲堂”课程首讲特邀著名作曲家教授陈晓勇先生担任主讲人,其演讲题目为“以意代形,返璞归真:音乐创作的诗意与灵性”。23级博士研究生及校内外诸多师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讲座开始,针对自己从事作曲事业多年的经历,陈晓勇教授首先提出了“我们为什么作曲?”这样自省式的问题,而这一问题似乎不仅是陈晓勇教授对其自身作曲生涯提出的诘问,同时也似乎是对参加讲堂的每一位作曲系同学的规箴。
陈晓勇教授对此作出自己的解答,即:音乐创作的重点,在于对本质与精神的追求,而非外在形式的执着。作曲不光是音符的排列组合,而是强调诗意的表达、情感共鸣以及灵性超越的思考和深度探索。
陈晓勇教授认为,以意代形意味着超越技法和风格,音乐承载着深层的情感哲思和精神体验;返璞归真则指对本源的回归,摆脱过度的复杂性,尊重听觉规律,让音乐回到纯粹和本真的状态。在理念和执行上体现东方哲学对艺术的理解,借此强调音乐创作对深度与本质的追求。此为陈晓勇教授关于该选题的初衷。
此外,陈晓勇教授还提到了“声音对人的直接影响和作用”这一重于其他理论和任何解释的观点——即声音的直接性与精神性。他认为,音乐一定要和听众有直接的互动关系,并且强调了“要注重聆听者的参与以实现意境的开放性”以及“从感性到理性的升华”这一音乐的最高目的。
对于这一标题的含义,陈晓勇教授将其总结为:“以意代形、返璞归真”并非否定形式或技法,而是强调音乐的最终目的,强调一种精神体验的传达。思考音乐的内在本质,而非表层的结构。其中重要的是在于以开放的心态聆听,体验音乐中蕴含的深远意境。
随后,陈晓勇教授通过他所创作的几部作品对其创作理念、创作手法进行剖析来阐明他的观点。
一、以意代形
《喑、晰、逸》创作于2004年,其编制为8件中国乐器和8件欧洲乐器组成——这或许是对陈晓勇教授所说的双重身份冲突的一种形式上的诠释。陈晓勇教授将该作品定义为一部内心化的“微型音乐剧场剧”(Musiktheater),在十分钟内呈现出极端对比的情感冲突。人声与乐器交织,游走于现实与想象之间,营造出碎片化、非线性的戏剧张力。其中的词选自《道德经》片段,但是在音乐中被高度抽象化,拟声化,几乎失去语义,转化为纯粹的声音与韵律。音乐通过突兀断裂、音色切换与紧缩时间,制造出仿佛经历“无数戏剧情节”的听觉体验。陈晓勇教授表示,这不仅是一部音乐作品,而是一次语言、情感与声音的试验 ,在超现实的声场中探索语义的消解与情绪的重塑。
陈晓勇教授将这部作品称为双重身份的冲突理论。所谓双重身份冲突或许是体现在生于中国但长年在德国学习的陈晓勇教授处于两种甚至多种文化之间,而他认为之后这段经历没有使他产生本质性的变化,而是增加了非常丰富的过程。
在聆听该作品之后,陈晓勇教授提出了五个供我们思考的问题:1.繁复与简洁;2.繁复与丰富(的区别);3.作曲家的意志与听觉感知;4.结构的复杂性与听觉可辨性的差距和“界限”;5.实际的音乐体验和对音乐的理解。
陈晓勇教授从四个方面来阐述自己的理解和做法——将作曲的焦点从主观的建构转向感知、转向更加关注听觉和情感的方式,这其中包括四点:一、从形式到即时体验:调整形式结构与结果的关系,强调各部分的相互关联。音乐的整体结构不再仅仅被视为一个固定的框架,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各部分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当焦点从形式转向感知时,音乐的聆听方式成为了关注点。聆听聚焦在对音色变化、微妙的节奏运动、力度对比、微分音等诸多元素所产生的作用之上,声音直接影响着听众的情绪与感受。关于这一点,陈晓勇教授进行了补充,即这一观点与其音乐的曲式结构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其中不存在任何已经被固定的曲式,而是每一种音乐、一个新的启发构思将会寻找一个新的结构;二、音响的质感与情感的传达:更加关注感知,注重音响的质感与细节;三、音乐的即时性与流动性:聆听过程转向感知上的即时性和流动性,更多注重感官体验。声音可能是不断演变的,体验感越过形式。四、把感知当作引导创作的核心:多种技术手段例如运用微分音程、噪音、音色变化等,音乐创作渐渐倾向音乐如何触发听众的情感反应和听觉感受,甚至可以成为创作的核心(手段及目的)。这样,音乐不仅是理性构建的结构,而是一场以触动人心为目的的、生动的听觉体验。
《蔟》创作于2009年,编制为笙(中国)、筝(日本)、长鼓与锣(朝鲜)以及小提琴与大提琴(西方)等多种乐器,以细腻而内敛的方式跨越文化与时代的边界。
陈晓勇教授采用极简手法,追求深意,音响层次疏密相间,徘徊在宁静与流动之间,于虚实交错中寻求微妙的平衡。美学风格深植于中国及东亚传统,注重余韵与空间感,而非西方先锋派的极端实验性探索。音色交织如同丝线相蔟,既独立又相互渗透,听觉上塑造出一种东方意境,使音乐仿若在时空中缓缓展开,留白之处尤显深远,语音之中自生意味。
陈晓勇教授表示以上两部作品均与文化交融,与一种新的音乐文化的诞生和成长有直接关系。籍由上述两部作品,陈晓勇教授阐述了关于对感知的过程、音乐元素的多样性、非固定形式三个方面的理解。他认为,首先感知不仅是过程,还是创作的基础。更加被关注的是声音如何被感知并引发听众的情感反应;其次,非常规的音乐元素的应用,如微分音程、噪音、音色的微变、空间(留白)、凝聚力等,这些都可以成为创作的核心内容,而不再仅仅是方式;再者,非固定形式则是不再以传统的音乐曲式为基础,而是采用更加灵活的结构——由表现需要而激发的“个性化”结构,注重听觉和感知的即时体验来与听众产生联系。
二、返璞归真
陈晓勇教授首先谈到了对简洁与丰富两者关系的思考。他认为,虽然极端的繁复可能产生困惑,尤其是当结构打破了常规听觉的期待和理解方式。复杂性也能够揭示出深层次的音乐美感,带领听众进入超越表面感知的体验。处理得当,则能够唤起更强烈的情感反应,创造出一种独特的精神和哲学的氛围。而简化能使核心更加直观,提升听觉识别能力,激发感官体验与精神反思的共鸣,有助于激发思考的主动性。
“简洁”意在去除冗余、保持精炼和明晰,它通过简练的元素展现出深度与意蕴;而“丰富”则是在简洁的基础上赋予层次、细节与变化,使音乐既有清晰的结构,又承载更深的情感与思想。丰富并非杂乱无章,而是多样性与内在秩序的和谐统一。因而,简洁与丰富相辅相成,简洁构建整体框架,为丰富性提供了空间和表达平台。
陈晓勇教授谈到了他的交响乐队作品《梦的颜色》(Colours of Dreams)中的最后两分钟,该作品是对“以意代形,返璞归真”这一理念的进一步的举例说明。基于完形心理学的闭合原则,闭合本身提供统一感,而其内部的多变性及近似混沌状态则与“外表”构成对立统一。在这一部分,复杂的内部动态挑战“外表”的整体单一性,从而形成一种具有推动性的张力。与此同时,内部的“无序”被包裹在统一的外形之中,在听觉体验上自然塑造出一个似乎可见的“形”。这一特质具体体现在和声的层次变化、配器色彩的丰富对比,以及多层次力度的相互交织之中。
三、诗意与灵性超越
对于这一标题所涵盖的内容,陈晓勇教授将之概括为:1.从感官之悦到心灵之领悟;2.文化意蕴、诗意表达、聆听的开放性;3.超越艺术——音乐作为精神体验;4.音乐超越单纯的声音事件,进入形而上学;5.超越美学与伦理的性质。
由此,陈晓勇教授阐述了他对于这一标题内容所引发的对作曲技术的思考与实践,即音乐并非单纯的声音事件,它可以超越瞬间的听觉体验,打开形而上的维度。音乐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精神体验——那么,哪些作曲技法能够实现这一维度的开启?
其一、“空间感”是音乐精神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教堂的音响特性,例如悠长的混响时间、反射类别,都可显著地增强着超越感。声音的交融、消散,形成一种悬浮感,使时间与空间交织在一起,进入不确定状态。
其二、根据物理的干涉原理(Interference-Prinzip),不同的频率相遇产生拍频、共振和复杂的声学图案。这种物理现象可被理解为音乐表达的一种更深层次的秩序。在音乐中有意地运用这些声学干涉效应,能够创造出既和谐又神秘的音响体验。
陈晓勇教授首先列举了他去年十一月在德国演出的作品《interference》,展示了把教堂的建筑声学以及声场特点当作乐器来使用的手法。按照陈晓勇教授的理念,这种在教堂中巨大空间的长时间混响,可以让音乐获得超脱感,使时间和空间交织进入不确定状态。同时,不同频率产生拍频、共振创造出和谐神秘的效果。与该作品使用近似手法的,是陈晓勇教授列举的另一部作品《解脱-人类安魂曲》,这部作品除了同样利用了教堂大空间、长混响的声学特点外,陈晓勇教授还有意的使用了按照泛音列构成的和声(泛音及泛音列和声研究——泛音和弦「Obertone-Chord」的运用)。
陈晓勇教授谈到,与十二平均律不同,纯正的泛音结构建立在自然声学规律之上,因而具有独特的纯净性,与声音的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直接相关。在音乐创作中,将纯正的泛音和弦与平均律音高结合,既可以制造绝对和谐,又可以在自然共鸣与传统和声系统之间制造一种张力,形成即传统又突破传统的音响关系。
陈晓勇教授向我们展示了《解脱——人类安魂曲》这部作品的乐器选择、特殊编制的设计以及演唱方式,既塑造了音乐的质感,也深刻影响其精神性。在这里,合唱与大量低音乐器如七把大提琴、低音提琴、大军鼓、Tam-tam等共同营造出深沉的共鸣,释放出大量自然泛音,并直接作用于听者的身体,而泛音吟唱(Obertone singing)则开启了另一重声响维度。
另外,这部作品受到藏传佛教与喇嘛诵经的启发,作品在音乐构造上超越了传统旋律的概念,以泛音共振为核心塑造出频谱性的音响场域。声音不再依赖旋律线条,而是通过泛音结构展开,在听觉之外触及身体共鸣,使聆听者进入一种超越感官的体验。
陈晓勇教授还补充道,空间、共振与泛音的相互作用,以创造一种不仅仅能够被“聆听”而是可以“感受:的音乐——一种不仅能触及听觉,更能在精神层面引发共鸣的音乐。当音乐超越自身的物质属性,它的意义便凸显出来。在这一层面上,以“意”代替了形式,音乐从单纯的结构构建转向对精神体验的追求,从而引导听众进入更深层次的感知。
陈晓勇教授总结道,音乐可以从声音事件通往形而上领域,唤起内心深处的情感和哲学思考,超越时间与空间,将听者带入一种沉思与觉悟的境界。通过相应的作曲技法与丰富的文化内涵,音乐可以成为一种跨物质的精神体验。他同时也对声音、空间、与超越感做出了总结:空间感是音乐精神的一个重要维度。教堂的空间与建筑音响效果,有助于通过长时间的混响营造出一种神秘的悬浮感,让声音在空中交织、消散。它仿佛打破了现实的界限,将听众带入一种超越时间的体验之中。与此同时,“干涉”原理的应用,使得不同频率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拍频、共振和复杂的声学图案。这些效应不仅仅是物理现象,更蕴含着一种内在的和谐与秩序,成为音乐中探寻神秘与秩序的载体。
四、藏传佛教的“听闻”与音乐的精神体验
陈晓勇教授还向我们介绍了《解脱——人类安魂曲》的创作背景,这部作品与他2023年的《冈仁波齐》构成一套近两个小时的音乐哲学史诗,是陈晓勇教授阅读《西藏生死书》、领悟其智慧与哲理之后孕育而生,旨在探讨“生与死”这一人类永恒命题,引领听众踏上关于生命轮回与觉悟的沉思之路。其中《解脱——人类安魂曲》是套曲的第一部分,分为两个乐章:一、“生”-生命从混沌中萌发、绽放,充满活力与希望,象征着对生命的礼赞与感恩;二、“死”-深邃而静谧,众生直面死亡的无常与净化力量,在和谐与宁静中完成转化,表达超越生死的精神升华。贯穿作品的六字箴言吟唱,象征着生命与死亡之间的净化与觉悟。男女混声合唱团的集体吟唱,表达灵魂的共同呼声;借助藏传泛音歌唱者的自然共鸣,传递解脱的深刻智慧;乐队与管风琴构建的宏大音响体现出时间、轮回与仪式的神圣感。巨大的管风琴不仅展现了仪式性的神圣感,更象征着超越种族、文化与信仰的适用于全人类的共同理念。通过融合东西方音乐传统,它应当成为世界和平与人类共同命运的纽带。作品以深沉而纯粹的音乐语言,搭建起人与自然、信仰与哲理之间的对话之境。它是一部献给人类朴实情感与哲学思考的音乐(史诗)作品,表达了死亡并非恐惧的终结,而是生命回归本源、转化与解脱的必经之路。
陈晓勇教授还分享了他对藏传佛教的“听闻”与音乐的精神体验的理解。他谈到,“听闻”是修行的重要方式之一。音乐可以通过深度聆听进入精神状态,成为觉悟的媒介。音乐不仅是表达情感的艺术,更是一种唤醒意识、开启智慧的通道。呼麦男低音歌手的诵经与泛音吟唱便是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低音吟诵不仅在内容上具有启示意义,其声音本身也承载着精神的力量。低频泛音共鸣与身体的自然振动相呼应,使听者不仅用耳朵去聆听,更是“用身心去感受”。合唱与低音乐器的结合创造出深沉的共鸣,是对仪式感的唤起。而泛音吟唱的运用,则能使音响结构超越旋律的概念,形成一种无边界的共振场,激发听者的沉思和内观。
结语
在讲座的最后,陈晓勇教授表示,他希望通过音乐触及人类内心深处,引发哲学沉思与灵魂觉醒。无论是利用教堂的空间体验、频率干涉所产生的神秘共振,还是通过泛音和谐以及听闻智慧,目标都是不断突破音乐的物质界限,使其以意义超越形式。他认为,这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已在他的音乐中得到的实践。在作品中,陈晓勇教授研究了空间、共振与泛音的相互作用,以创造一种不仅仅可以被“聆听”,而是可以“感受”的音乐——一种不仅能触及听觉,更能在精神层面引发共鸣的音乐。当音乐超越自身的属性,便使意义得到凸显。此处意义替代了形式,音乐从单纯的构建转向对精神体验的追求,从而引导听众进入更深层次的感知。正如《安魂曲》与《冈仁波齐》这套作品所展现的那样,陈晓勇教授希望音乐不仅是对生命的礼赞,也是一种对死亡与重生哲理的深刻思考,最终引领听者踏上一场关于生命本质与人类统一性的心灵之旅。
(撰稿:黄扬辉)